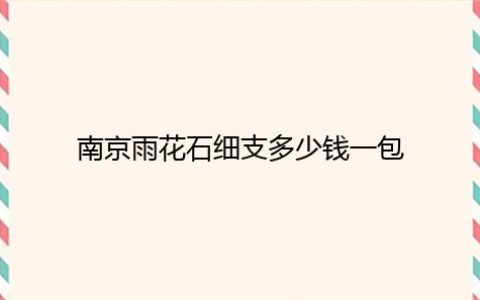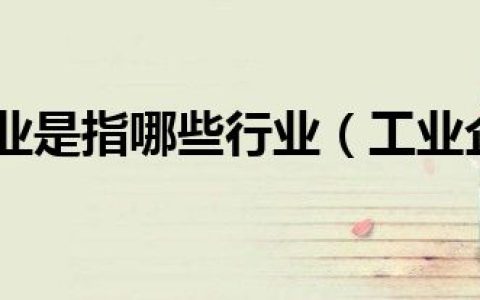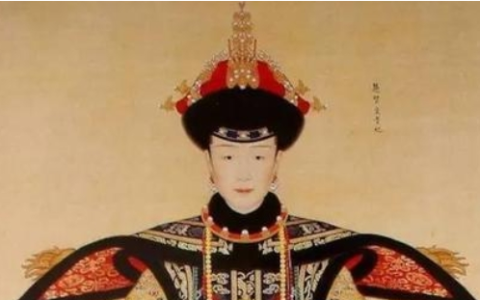虽然有些人不了解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的缘由,也不了解切尔诺贝利爆炸事故的后续情况,但是大部分人都应该听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。这是人类发展至今为止最大的一次败笔,到现在为止人类造成核事故有两次,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一次就是切尔诺贝利事故,另一次则是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。

相比于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来说,切尔诺贝利更加严重。由于爆炸的核反应堆至今都处于工作状态,所以切尔诺贝利依然还有核辐射存在。而且这种辐射程度居高不下,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持续几百年,甚至是几千年的时间。而在这些年当中,切尔诺贝利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。

在网上有些人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,能否用小型核武器对切尔诺贝利的反应对进行轰炸,从而让其充分的发生反应。这样一来,将能够加速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的反应速度,尽快消耗掉这些核反应堆的材料。这样一来,切尔诺贝利将在不久之后就能够供人类居住了。

这种想法很天真,但其实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。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核武器虽然和核反应堆采用同样的工作原理。但是两者反应的条件却不相同,核武器爆炸需要超临界质量,而核原料反应则需要的是临界质量。也就是说即便是用核武器进行爆破,也不会让核反应堆的核原料发生爆炸并且加速燃烧。这样一来,只能够将核反应堆的核原料炸裂开来,所以这种做法只能够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,会再次让切尔诺贝利的核反应堆发生大规模扩散。

现在看来核能既造福了人类,同时也毁灭了人类。如何安全的使用核能,避免核能对人类造成伤害,才是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。
本报讯 35年前,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世界上最严重的核事故。35年后,裂变反应再次在已损毁设施内的铀燃料堆中阴燃,“就像烧烤坑里的余烬”。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核材料化学家Neil Hyatt说。现在,科学家正忙于确定这些反应是会自行消失,还是需要采取干预措施以避免另一场事故。
据《科学》报道,乌克兰基辅核电站安全问题研究所(ISPNPP)的Anatolii Doroshenko近日在拆除反应堆讨论会上说,传感器追踪到一个人们无法进入的房间里不断流出新增的中子,这是一种裂变反应的信号。
“有很多不确定性。”ISPNPP的Maxim Saveliev说,“我们不能排除事故的可能性。中子数量上升缓慢,这表明管理人员仍有几年时间找出遏制威胁的方法。”
核废墟中的核裂变,或者说临界状态,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。1986年4月26日,当该核电站4号反应堆的部分堆芯熔化时,放射性物质流入反应堆大厅的地下室,并硬化成所谓的含燃料材料(FCM),其中含有约170吨放射性铀,占原始燃料的95%。
一年后,相关部门建设了一座由钢筋混凝土构成的、雨水可以渗入的“避难所”,以存放4号反应堆“遗体”。水减慢了中子的速度,从而增加了它们撞击和分裂铀核的概率。但是,暴雨有时会使中子计数飙升。
1990年6月,一场大雨后,一位科学家冒着暴露于辐射的风险,进入受损的反应堆大厅,在FCM上喷洒了硝酸钆溶液,这种溶液可以吸收中子。他和同事都担心FCM可能变成临界状态。几年后,相关部门在“避难所”房顶上安装了硝酸钆喷洒器,但喷雾不能有效渗透到一些地下室。
2016年,一座耗资15亿欧元的新安全设施封闭了“避难所”,以便稳定并最终拆除反应堆。新设施可以阻挡雨水,自从它被安置以来,“避难所”大部分区域的中子数一直保持稳定或在下降。
但在一些区域,相关数字开始慢慢上升。例如,近4年中,305/2号房间的中子数几乎翻了一番。ISPNPP的模型表明,在某种程度上,燃料的干燥使中子在裂变铀核时更有效。“这是可信的数据,只是还不清楚机制是什么。”Hyatt说。
这一威胁不容忽视。随着水不断退去,人们担心“裂变反应会呈指数级加速”。Hyatt表示,这会导致“不受控制的核能释放”。
应对新威胁是一项艰巨的挑战。305/2号房间的辐射水平使人们无法靠近并安装传感器,由于它被埋在混凝土下面,也无法喷洒硝酸钆。一种办法是开发一类可长时间承受强辐射的机器人,让它在FCM上插入硼柱,吸收中子。
不过,复燃的核裂变反应并不是唯一的挑战。由于被强辐射和高湿度包围,FCM正在瓦解并产生更多的放射性尘埃,使拆除“避难所”的计划变得更为复杂。